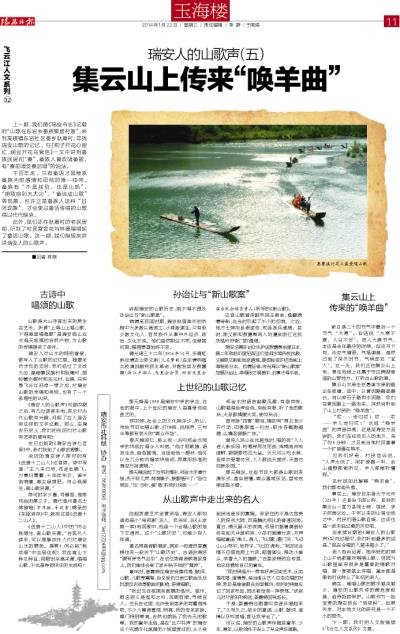飞云江人文系列
32
瑞安人的山歌声(五)
集云山上传来“唤羊曲”
上一期,我们随《瑞安市志》记载的“山歌在东岩乡畲族聚居村落”,来到高楼镇东岩社区畲乡驮庵村,寻找瑞安山歌的记忆。在《桐子开花心里红,豌豆开花乌紫色》一文中讲到畲族民居和“寮”,畲族人喜欢唱畲歌,有“寮前唱爻寮后唱”的说法。
千百年来,只有畲语才是维系畲族内部感情和团结的唯一纽带。畲族有“不是叔伯,也是山哈”、“唠歌唠到天大光”、“畲话成山歌”等现象,也许正是畲族人这种“封闭现象”,才会使以畲话传唱的山歌得以代代继承。
此外,我们还在驮庵村的老民居前,听到了村民雷金花与林德福唱起了畲话山歌。这一期,我们继续来讲讲瑞安人的山歌声。
■记者 林晓
古诗中
唱颂的山歌
山歌是大山孕育出来的原生态艺术。所谓“上得山上唱山歌,下得海里唱渔歌”是瑞安临山近水得天独厚的自然产物,为山歌的传唱提供了条件。
瑞安人对山水的特别眷爱,都写入了山歌的记忆里。随着采访步伐的迈进,我们经过了文成大峃、高楼镇民族村和驮庵村、湖岭镇光辉村和东元村、仙降、马屿等飞云江沿岸一带之后,对瑞安山歌的传唱和类别,也有了一个条理性的认识。
《瑞安人的山歌声》刊登四期之后,有几位读者来电,表示对古代山歌有兴趣,问起了古人是否有这样的文字记载。那么,在瑞安历史上,我们的先民们对山歌有怎样的描写呢?
在已出版的《瑞安古诗七百首》中,我们找到了山歌的踪影。
宋时的瑞安诗人陈可时有《送裴十二山人》这首诗。诗中写道:“主人来已早,花逐杜鹃飞。万事归霜鬓,十年犹布衣。溪平流响瘦,春去绿荫肥。何必桃源住,南山歌采薇。”
陈可时字少鲁,号懒吾,是陈则翁的第三子。清代温州著名士绅曾唯(字岸接,号近堂)辑录的《东瓯诗存》中,就有这首《送裴十二山人》。
《送裴十二山人》中的“何必桃源住,南山歌采薇。”在现代人读来,可以理解成先人们对瑞安山水的赞扬。是啊!何必到“桃花源”中去居住呢?我在南山下种瓜种豆,闲暇时采桑采薇,唱唱山歌,不也是种很快乐的生活吗?
孙诒让与“新山歌案”
讲起瑞安的山歌历史,就不得不提及孙诒让与“新山歌案”。
晚清至民国时期,瑞安旅居海外的侨胞中大多数以做苦工、小商贩谋生;只有极少数文化人、官员旅外从事中外经济、政治、文化交流。他们虽然职业不同,但爱国初衷、强国愿望始终不变。
清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4月,乐清虹桥反清志士陈又新(又名梦熊)在乐清明强女校演说鼓吹民主革命,并散发其友敖嘉熊(浙江平湖人,光复会会员,时任光复会温台处会馆负责人)所写的《新山歌》。
这首山歌宣传鼓吹民主革命、推翻满清帝制,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。之后,地方士绅向县衙密告,知县派兵逮捕。其时,陈又新和敖嘉熊两人均遭到浙江巡抚及温州府衙门的通缉。
瑞安名儒孙诒让先护送敖嘉熊东渡日本,第二年转赴印度尼西亚爪哇泗水埠侨校执教。又接陈又新到他家避难,旋即秘密护送他到上海转赴日本。后清廷省、府当局以“新山歌案”加罪孙诒让,幸得张之洞援手,此事才得平息。
上世纪的山歌记忆
缪天舜是1959届瑞安中学的学生,在他的眼中,上个世纪的瑞安人是喜爱传统曲艺的。
那时候,社会上的文化娱乐少,所以,传统节目如唱山歌、打快板、说相声、三句半等都有很大的“群众市场”。
缪天舜回忆,班上有一名叫郑金水同学的快板打得令人叫绝。“他才思敏捷,语言生动,音色圆润。当场给他一题材,他可以在几分钟内编成快板词,即席用标准的瑞安方言演唱。”
缪天舜说起了当年的情形,郑金水手拿竹板,先干咳几声,润润嗓子,接着唱开了:“各位同志,‘汪’勿吵,接‘落’听我打快板……”
郑金水的语言幽默风趣,有滋有味。山歌唱得绘声绘色,有板有眼,听了他的歌后,大家都捧腹大笑,前仰后合。
宣传除“四害”期间,唱的有“男女老少齐行动,四害麻雀一扫空;蚊虫苍蝇跑福建,尖嘴老鼠躲广东。”
宣传人民公社优越性时,唱的有“人人进入新乐园,吃喝穿用勿用钱,鸡鸭鱼肉味道鲜,顿顿要吃四大盆。天天可以吃水果,各样衣服着勿完,人人都说天堂好,天堂勿如新乐园。”
缪天舜说,这些节目大都是山歌的表演形式,通俗易懂,群众喜闻乐见,宣传效果还挺不错。
从山歌声中走出来的名人
说起表演艺术家黄宗洛,瑞安人都知道他是个“电视剧”名人。而当年,在《土家第一军》电视剧中,他是一个会唱山歌的地下交通员。这个“山歌历史”,可能少有人知道。
著名男高音歌唱家、国家一级演员姜嘉锵也有一段关于“山歌历史”。古语说得好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,在这位男高音歌唱家身上,我们能体会到了家乡给予他的“营养”。
童年时,姜嘉锵在瑞安受莲花落、鼓词、山歌、儿歌等熏陶,后又受抗日救亡歌曲及反饥饿反内战等歌曲的影响,深爱唱歌。
“我出生在祖国东南隅的温州。温州,顾名思义是温和之州,风调雨顺,气候宜人。生长在这里,也许受到更多的雨露润泽吧,不少人嗓音圆润、明亮,我的母系家族,嗓门特别嘹亮,自然也就给了我先天的歌喉。我的童年生活,是在‘比户书声’的瑞安这个充满文化氛围的小城里度过的,从小受到民间音乐的熏陶。我家住的不是达官贵人的深宅大院,而是鳞次栉比的普通民房。夏日,满天星斗的夜晚,邻居们摇着蒲扇纷纷来到天井里纳凉,小孩们围着竹床,齐声唱起童谣‘燕儿,燕儿,飞过殿;殿门关,飞过山;山呀平,地呀平,飞过打虎岭。’有时还会情不自禁地爬上竹床,踮着脚尖,挥动小拳头,学着大人的撞歌。”在姜家锵的自传里,他这样描绘自己的童年。
“那时候温州一带有好多民间艺术,比如莲花落、道情等,每当街头艺人边走边唱的时候,我总是偷偷跟在后面模仿,有的时候竟忘记了回家吃饭,因此被母亲一阵责骂。”谈到儿时对音乐的痴迷,姜嘉锵回味悠长。
于是,姜嘉锵也跟着叫卖音乐唱起来了。“久而久之,故乡的童谣、山歌、鼓词、道情以及叫卖唱,都让我学会了。”
可以说,瑞安的山歌声伴随其童年、少年、青年,以致他终于走上了专业声乐道路。
集云山上
传来的“唤羊曲”
前日是二十四节气中最后一个节气“大寒”。俗话说“大寒不寒,人马不安”。进入大寒节气,本应是全年最冷的时候。但这月下旬,冷空气偏弱,气温偏高,虽然已到了深冬时节,气候却还“宜人”。这一天,我们正往集云山上走,想在地域上还属于市区锦湖街道的山野地方,打听点山歌的事。
集云山水库去往愚溪水库的路正在修建,其中,以黄泥路路面最长,间以碎石子路和水泥路,我们在黄泥路上一路走来,突然间听到了山上村民的“唤羊曲”。
“哎……走归哎!哎……哎……羊儿走归哎!”这组“唤羊曲”的声音洪亮,还是用瑞安方言讲的。我们在还没见人的地方,走了约5分钟,才见到当地村民拿着一个扩音器在唤羊。
见我们好奇,村民告诉说,“人声太低了,用扩音器一叫,全山遍野都能听见,羊儿都能听懂呢。”
见村民如此解释“唤羊曲”,我们都有些失落。
事实上,瑞安自东晋太宁元年(323年)迁县治于邵公屿,其后的集云山一直为县城士绅、居民、学子郊游之处。千年以来的山居生活之中,村民们唱山歌自娱,应该也是一段未经记载的历史吧。
在连续五期的《瑞安人的山歌声》采访过程中,我们听到最多的话是,“现在会唱的人越来越少了。”
老人告诉记者,她年轻的时候上山干活都喜欢唱唱山歌,但因为山歌里面有很多是露骨的情歌对唱,曾一度被禁止传唱,基本都是像他们这种上了年纪的老人。
确实,能唱山歌的歌手越来越少,瑞安的山歌失传的濒危度极高,亟待抢救保护。山歌作为一批宝贵的瑞安民俗“活资料”,如果失传,对本地文化的研究是一个不小的损失。
下一期,我们的人文版继续《飞云江人文系列》文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