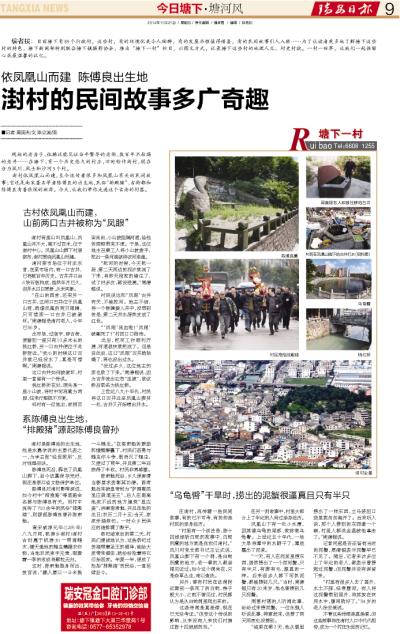依凤凰山而建 陈傅良出生地
湗村的民间故事多广奇趣
■记者 黄国夫/文 陈立波/图
ui bao
Tel:6608 1255
塘下一村
R
编者按:目前塘下有89个行政村,这些村,有的环境优美令人陶醉,有的发展历程值得借鉴,有的民间故事引人入胜……为了让读者更多地了解塘下这些村的特色,塘下新闻部特别联合塘下镇摄影协会,推出“塘下一村”栏目,以图文方式,记录塘下这些村的地理人文,村史村貌。一村一世界,让我们一起保留心底最温馨的记忆。
残垣的老房子、依稀还能见证当年繁华的老街、数百年不枯竭的老井……在塘下,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庄,旧时称作湗村,现在分为凤川、凤士和沙河3个村。
湗村依凤凰山而建,至今流传着很多和凤凰山有关的民间故事;它还是南宋著名学者陈傅良的出生地,民俗“排殿猪”、古街都和陈傅良有着很深的渊源。今天,让我们带你走进这个古老的村落。
古村依凤凰山而建,
山前两口古井被称为“凤眼”
湗村有座山叫凤凰山,凤凰山并不大,高不过百米,位于湗村中心。凤凰山山脚下村居密布,湗村围绕凤凰山而建。
湗村菜市场位于村庄东首,在菜市场内,有一口古井,已有数百年历史。古井井口由6块石板构成,虽然年月已久,但井水日日更新,从未间断。
“在山的西首,还有另一口古井,这两口古井位于凤凰山前,就像凤凰的两只眼睛,只可惜那一口古井已被破坏。”周德银是湗村老人,今年已86岁。
出市场,过庙宇,穿古街,便看到一座只有10多米长的桃红桥,另一口古井便位于此桥附近。“我小的时候这口古井就已经没水了,真是可惜啊。”周德银说。
这口古井如何被破坏,村里一直留有一个传说。
桃红桥所在处,原先是一座小山坡,将村中河流截为两段,往来行船极不方便。
邻村有一位地主,家拥百亩良田,小山坡阻隔河道,给他的商船带来不便。于是,这位地主召集工人将小山坡凿平,挖出一条河道欲将该河连通。
“挖河的时候,今天挖一段,第二天两边的泥沙就流了下来,将昨天刚挖的堵住了,试了好多次,都没进展。”周德银说。
村民说这和“凤眼”古井有关,不能挖河。地主不信,将一个铁棒插入井中,没想到的是,第二天井水居然变成了红色。
“‘凤眼’流血啦!‘凤眼’被戳死了!”村民口口相传。
此后,挖河工作顺利开展,河道很快就挖成了。但是自此后,这口“凤眼”古井就枯竭了,再也没出过水。
“没过多久,这位地主的家也败了下来。”周德银说,因为古井流出红色“血液”,故该桥后取名为桃红桥。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村民将这口古井迁至凤凰山脚另一处,古井又开始喷出井水。
系陈傅良出生地,
“排殿猪”源起陈傅良曾孙
湗村是陈傅良的出生地,他是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,为学主张“经世致用”,反对性理空谈。
陈傅良死后,葬在了凤凰山脚下,至今该墓保存完好,现在是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。
陈傅良对湗村影响深远,如今村中“相堂路”等道路命名都与陈傅良有关。而村中流传了700余年的民俗“排殿猪”,则源起陈傅良曾孙陈肃勉。
南宋咸淳元年(1265年)八九月间,帆游乡湗村(湗村古时属于帆游乡)一带闹蝗灾,铺天盖地的蝗虫糟蹋农作物,当地农民束手无策,眼看着一季的收成将颗粒无归。
这时,陈肃勉挺身而出,放言说:“鄙人愿以一斗米换一斗蝗虫。”在陈肃勉的鼓励和慷慨解囊下,村民们奋勇与蝗虫作斗争,既消灭了蝗虫,又度过了荒年,并且第二年还获得了丰收。村民非常感激。
陈肃勉死后,乡人便奏请当朝要求表彰其功德。陈肃勉后来被皇帝封为“护国惠民显应崇道圣王”,后人在距离他家不远的地方建筑“显应庙”,供奉陈肃勉,并且在他的生日(农历二月十五)当天,家家杀猪祭祀。一时众乡民供应的猪排满了殿宇。
祭祀结束后的第二天,村民们虔诚地认为,这些祭祀过的猪带着圣王的福泽,能给大家带来福佑,就纷纷抢着将它们抬回家。年复一年,便成了抢抬“排殿猪”的民俗,一直延续至今。
“乌龟臀”干旱时,捞出的泥蟹很逼真且只有半只
在湗村,流传着一些民间故事,有的已不可考,有的却是村民的亲身经历。
“村里有一个说法是,陈十四娘娘斩白蛇的故事中,白蛇所藏的地方就是在我们湗村。”凤川村党支部书记王让式说,凤凰山脚下有一个洞,是白蛇所藏的地方,老一辈的人都亲眼见证过;如今这个洞尚在,只是杂草丛生,难以查找。
另外,曾有村民在该洞附近看到一条死了的白蛇,筷子般大小,之前不曾见过,村民都认为是从白蛇洞里爬出来的。
这些传闻是真是假,现在已无法考证。“但受这个传说的影响,从来没有人来我们村演过陈十四娘娘的戏。”
在另一则故事中,村里大部分上了年纪的人有过亲身经历。
凤凰山下有一处小水潭,因其像乌龟的尾部,故称做乌龟臀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一场大旱将潭中的水晒干了,潭底露出了泥浆。
“一天,有人在泥浆里捞东西,居然捞出了一个泥河蟹,只有半只,有脚有毛,跟真的一样。后来很多人都下河抓泥蟹,都能捞到几只。”当时,周德银只有20来岁,他也曾捞到几只泥蟹。
周围村落的人听闻此事,纷纷过来捞泥蟹。一位永强人听说此事,特意赶来,但捞了两天两夜也没捞到。
“结果在第3天,他从湖里捞出了一样东西,立马装到口袋里就匆匆离开了。后来听人说,那个人捞到的东西像一个碗,村里人都说金盘被他拿走了。”周德银说。
记者问起是否还留有当时的泥蟹,周德银表示泥蟹早已不见了。随后,记者采访多位上了年纪的老人,都表示曾捞起过泥蟹,但泥蟹并没有保留下来。
“村里有很多人去了国外,水土不服,经常腹泻。有人将这泥蟹带到国外,将其放在饮用水中,腹泻就好了。”84岁的老人徐安斌说。
不管这些传闻是真是假,但这些故事将在湗村人口中代代相传,成为一个村庄永恒的记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