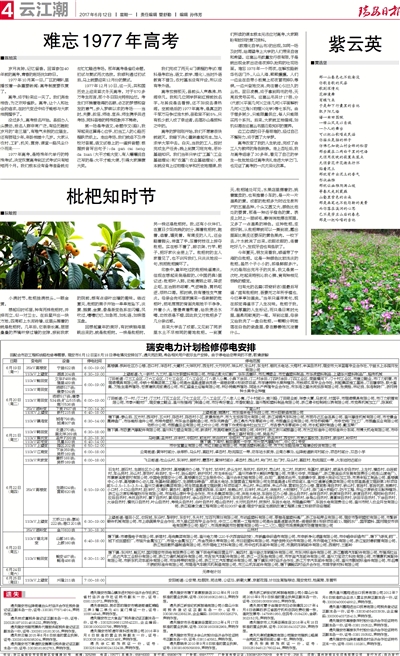难忘1977年高考
■陈旭滨
岁月流转,记忆留香。回首参加40年前的高考,青春的赶场犹如昨日。
1977年10月某一日,厂区的喇叭里播放着一条重要新闻:高考制度要恢复了。
高考,终于盼来这一天了。我们奔走相告,为之欢呼雀跃。高考,让个人和社会的追求,在时代变迁中终于能够与大家相拥握手了。
没过多久,高考报名开始。县招办人头攒动,报名人群非常广泛,有经历蹉跎岁月的“老三届”,有稚气未脱的应届生,还有弱冠少年,年龄相差十几岁。大家从农村、工矿、机关、营房、课堂一路风尘仆仆而来……
1977年高考,是特殊年代举行的特殊考试,决定恢复高考到正式考试只有短短两个月。我们根本没有备考准备就匆匆忙忙踏进考场。那年高考是省级命题,初试与复试两次选拔。我顺利通过初试后,马上就要迎来12月份的复试。
1977年12月10日,这一天,共和国历史上迎来首次冬天高考。对于570多万考生而言,那个冬日阳光特别灿烂。考生们怀揣着难得的名额、忐忑的梦想和奋发的意气,步入梦寐以求的考场……当时,夫妻、叔侄、师徒、官兵、师生携手共进考场、同科答卷的特殊现象并不稀奇。
第一场是考语文,命题作文《路》,我写起来还算得心应手,初当工人的心路历程跃然纸上。走出考场,我们就迫不及待校对答案,语文试卷上的一道拼音题(根据拼音写出句子):da gan cai neng da bian (大干才能大变),有人嚷嚷说自己写的是:大干才能大便,引得大家捧腹大笑。
我们完成了两天4门课程的考试(理科是考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理化),当时外语教育不普及,农村基本没有开设,所以没有考外语。
高考放榜那天,县前头人声鼎沸、热闹非凡。我和几位同学挤到红榜前找名字,与其说是去看榜,还不如说去凑热闹。空前绝后的1977年高考,是真正的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,录取率不到5%,只有极少数人成了幸运者,名落孙山是预料之中的。
高考的梦刚刚开始,我们不愿意很快就破灭。我暗下决心重新拿起书本,加入求学大军中去。白天,当我的工人,按时完成生产任务;晚上到复习班充电,恶补基础知识。我们当年只学过“工基”(工业基础理论)和“农基”(农业基础理论),根本就没有上过物理化学和历史地理课,我们所读的课本根本无法应对高考,大家期盼有较好的复习资料。
《数理化自学丛书》的出现,如同一场及时雨,给渴望考上大学的人们带来自信和希望。这套丛书数量发行很有限,于是就出现全家出动连夜排队抢购的壮观场面。难忘1978年一个雨夜,在解放路新华书店门外,人山人海、熙熙攘攘。人们一边坐在自带小板凳上彻夜冒雨排队等候,一边兴奋地交流、向往着心仪已久的丛书。翌日凌晨,终于拿到购书的号,天亮后凭号买书。这套丛书共计17册,分《代数》《平面几何》《立体几何》《平面解析几何》《三角》《物理》《化学》等七系列。由于僧多粥少,只能限量供应,每人只能限买两个系列。后来,大家就互相借阅,如饥似渴在这套丛书里汲取知识的营养。
边工边读的日子是艰难的,经过自己不懈努力,终于圆了大学梦。
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,完成了由工人为教师的角色转换。走上杏坛后,我与高考结缘了30多年,看见了自己的学生一批批地经过高考洗礼走进大学之门,也见证了高考的一次次深化改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