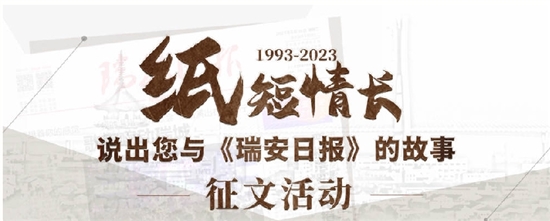我始终对《瑞安日报》充满着感情。我的喜怒哀乐都被《瑞安日报》妥善保存着,它见证了我的点滴辉煌、些许挫折,以及那些悲喜交加的历史时刻。我与它相恋相爱了26年并且一直持续下去。时间愈久,致敬之情愈加浓烈。在瑞安这片人杰地灵的大地上,它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最有才华的人,甚至在这些人的生命中引领着他们。
我的精神世界日渐丰盈得益于《瑞安日报》的滋养。1997年,18岁的我刚踏上工作岗位,不擅社交,于是躲进书里成一统。每当教学之余,就前往位于万松路上的瑞安市图书馆。走进三楼阅览室,我靠窗坐下,第一个翻阅的便是《瑞安报》。那时,它还不是日报,一周发行两次,后来变成一周三次,再后来逐渐发展壮大才改版升级为《瑞安日报》,从小张排版到对开八版,越来越大气。第一次翻阅它,我就有一种向往,如果我的文字也能变成铅字印在上面那该多好哇。没想到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。有一天晚上,我因在图书馆逗留过晚,回到学校被关在宿舍铁拉门外。那道门在平日极难开,钥匙在锁孔里上下左右寻找角度,不得法。黑夜沉沉,夜风凉凉,惊恐、无助、压抑、愤懑,各种情绪在心中发酵。由此,想到自己的人生,前途迷茫,一如这扇铁拉门,看得见却打不开。那一夜枯坐在办公室,奋笔疾书爬格子。一篇《开门》一气呵成。再折返铁拉门处,钥匙插入锁孔,轻轻一扭竟然打开了。好像冥冥中我吃的闭门羮就是为了遇见缪斯女神。
很幸运,第一次给《瑞安报》投稿,竟然在副刊上登了出来。《开门》为我打开了文学之门。怀揣着那张印有金春妙的报纸,我整整兴奋了一周。此后散文、小说频频见报,用过妙妙、凡心等笔名,但是更多的是署真名。那真是文学的黄金时代,副刊成了很多人的精神食粮。后来《瑞安日报》副刊版停刊小说稿,只发散文和诗歌,我一直引以为憾。
1999年,报社组织一批优秀通讯员到泽雅采风。我见到了如雷贯耳的作者和名家,对每个人都诚惶诚恐,毕恭毕敬。那天下午,我们在泽雅山庄开座谈会,会上主持人说不想喝酒的话要发言。我自知不会饮酒,赶紧抢先发言。洪善新老师觉得我讲得实在,鼓励我写出来。后来题为《多写写阳光下的好心情》发在《瑞安报》的内部“编通往来”上。当晚还举办了舞会,一部分人跳舞,一部分人聚在大露台看星星,聊文学和人生。第二天我们又在大露台合影留念。可惜那张照片我至今都没看见,我只记得照片里的很多人多年以后成了名编辑、名记者、名作家。
20年后我参加省文联举办的青年作家研修班学习,班主任在开班典礼上说 “新荷作家班是文学浙军的黄埔军校,从这里走出了不少在全国很有影响力的作家”。我的目光越过横幅上红色大写的“新荷”二字,遥想起泽雅山庄的联欢,啊,瑞报也是瑞安文学届的“黄埔军校”啊,多少文人从这里“毕业”,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
我最初的编辑是马邦城老师,我非常敬重他。记得报社曾招考过特约记者,很多文学青年都去考。我也不例外,并有幸考上。分在副刊部的共有三人,另两人是高泉印、王永乐,都是教师。我们走进当时位于西门一处民房的报社小楼,木地板嘎吱作响,但在我眼中就是文学圣地。马邦城老师清瘦,目光睿智,见到稚嫩的我们一点架子都没有。他鼓励我们多写稿,写好稿。得知我来自林垟,马老师的话匣子打开,回顾自己年轻时在林垟插队的往事,并嘱咐我去翻看族谱,挖掘金家名人金嵘轩的故事。前后二十年,我先后多次回到林垟,找族长公翻族谱,到祠堂寻访先人的故事。这段隐秘的往事我从未对人提起,也未曾写过金家的只言片语,但文学创作需要实地走访是马老师教给我的第一课。后来,我多次实践这一理论,并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深耕下去。
交集最多的是孙伟芳编辑。某年“五四”青年节,孙编组织了一批比较活跃的副刊作者聚会。从文学青年到文学中年,我们回顾往事展望前程,有说不完的话。席间,孙编得知我正在创作长篇纪实文学,提出连载想法,但是这本书正跟作家出版社签订合同,走出版流程,我婉拒了她。孙编却毫无不快,一如继往爱惜我,在她任上我的创作灵感不断被激发,有时甚至一周连发两稿。
副刊在陈良和编辑手中,又推陈出新,独创的文字加朗诵让点击量暴增。《瑞安日报》推出的第一篇朗读版是我的《掸新图谱》,由曾晨老师朗读,App链接一经上线,点击量蹭蹭上升。因为陈编,我认识了很多朗诵家和读者,他们的点评和互动,让我创作激情高涨。在这之前,我已悄然转为小说创作,很少发报纸副刊,因为陈编的创新和频频约稿,我重燃了散文写作的热情。
当然,我经历的编辑还有很多,如华小波、王海燕、林长丰、金锦潘、谢瑶等编辑,他们就像我生命中的灯塔,照亮我通往文学之路。《瑞安日报》是我文学梦的起源地,在它复刊三十周年之际,祝愿它越办越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