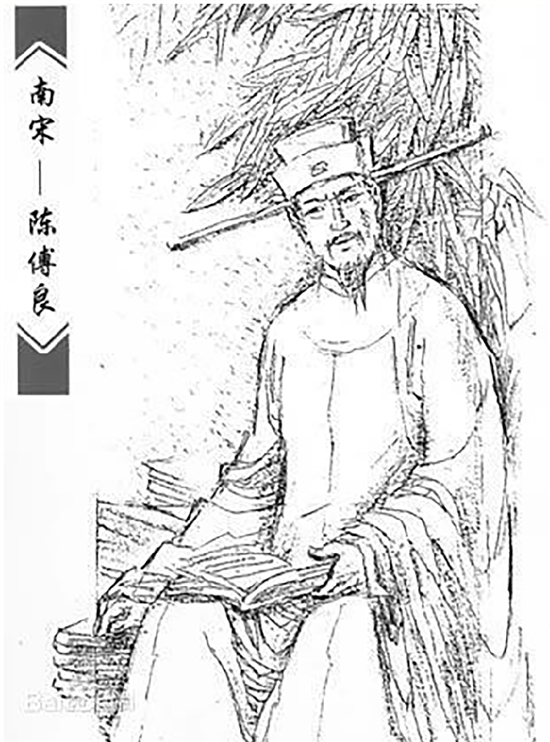你可知,在瑞安汀田岑岐山麓,曾有一座鲜为人知、颇具规模的宋代私家园林——赵园?有人说,它为瑞安四大名园之一(其他3处分别是北门沈园、第一桥郑园、西门寄园),陈傅良、蔡幼学等学者儒士频频造访,为之痴迷,并留下许多诗词佳句。赵园远去千年,仿佛是时间遗落的珍珠,静静地躺在历史的长河中,等待着后人揭开神秘的面纱。
诗中的“赵园”
“脉脉循檐水,林林夹岸山。令儿从竹下,领客入云间。稠木客人过,悬崖着手攀。从今名字出,不到径苔斑。”读着陈傅良的《游金岙赵园》,笔者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隧道,沿着一条窄窄的竹间石径,回到了那个岑岐山麓静雅深邃的私家园林。这里,林木葱郁,清泉潺潺,鸟语花香,亭台楼阁,充满了宋人的风雅与诗意。
诗的作者陈傅良是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,出生于南宋绍兴七年(即公元1137年),字君举,号止斋,人称“止斋先生”,瑞安湗村(今属塘下镇罗凤)人。青年时曾以教书为业,后主讲于茶院寺之南湖塾,温瑞一带小有名气,后于乾道八年中进士,官至宝谟阁待制、中书舍人兼集英殿修撰。中进士后授泰州教授,仍在家教书。后任职湖南,公余在岳麓书院讲学,门墙极盛。卒于1203年,谥文节。为学主“经世致用”,反对性理空谈,与同时期的学者陈亮近似,世称“二陈”。著有《止斋文集》《周礼说》《春秋后传》《左氏章指》等作品。其中,《八面锋》为宋孝宗击节赞叹,御赐书名,流传甚广。
陈傅良与赵园结缘颇深,教书或讲学之余,常常携友同游赵园,诗酬来往,留下了一定数量的诗词,比如《游金岙赵园赋海棠梨花呈留宰》《赴留宰宝坛之集因和蕃叟弟赵园韵》《游赵园》等等。彼时,赵园作为一个“文化驿站”,吸引众多文化名士慕名前来雅集、采风,留下了为后人称道的诗文书画、摩崖石刻。周围至今存留翠阴洞摩崖题记、名刹宝坛寺等遗迹。
赵园所在的金岙,大概位置就在现今汀田街道金后。据《瑞安县志·氏族门》记载:“金氏有汀董乡之金岙,一百户,望族彭城。”民国《瑞安县志稿》和金后《金氏族谱》载,金姓于宋自台州太平县迁此地,以姓名村。明清为金岙庄,属清泉乡,清光绪属清泰乡。民国时称金岙,1931年属汀川乡,1935年属汀董乡,1946年属董岙乡。1949年置金前、金后村,属汀田乡;1961年改称金前、金后大队,属汀田公社;1984年复置金前、金后村。2019年,金前、金后、凤岙、山上陈合并成为金凤社区。
从陈傅良存世的350多首诗词歌辞中,写赵园的诗词就多达六七首,占比高达2%左右,说明赵园当时较高的知名度,以及陈傅良对赵园的偏爱。文史专家宋维远老师指出,提及赵园,不得不提“北湖”和林氏家族、赵氏家族、沈氏家族。他给笔者画出了北湖、赵园、塘岙、湗村(今塘下罗凤)、东郭(可能指现塘下赵宅)以及温瑞塘河的大致线位图,陈傅良住湗村,常通过集云山古道或水路,来往于赵园、北湖等地,赵园刚好是以上诸地的枢纽。此外,陈傅良与林氏家族、赵氏家族、沈氏家族有多重姻亲关系。陈傅良的妻子张幼昭是温州城南名士、元丰九先生之一张晖的孙女、张孝恺(字思豫)的女儿,而张孝恺又娶“元丰九先生”之一赵霄(瑞安人)的孙女为妻。
“上巳所余春有几,不堪风雨付春愁。君能载酒知谁侣,我欲看花不自由。倚岸小舟谋未定,隔林斜日故相投。莓苔踏遍篝燈去,收拾残红插满头。”这是陈傅良与道甫(王自中)、子宜(徐谊)、行之(蔡幼学,陈傅良弟子)等人载酒同游赵园的情景。能与三五好友同游赵园,把烟雨时节的江南美景和对逆境的愁绪不落痕迹地融汇在一起,也算人生一大惬事。此诗出自《瑞安宰刘伯协载酒游赵园,叔静、道甫、子宜、行之同集,小雨喜霁》。
“主人避客竟何之,雨过停桡落日迟。赖有畦丁曾识客,来禽花送二三枝。”这首七言绝句则出自他的《游赵园》。此诗写的是游赵园,实际上是访友,因为陈傅良与园主是好朋友。此诗前两句写去拜访朋友的过程,三、四句写不遇后园丁却认出了自己这个常客,送上几枝来禽花,把访友不遇的不快全部冲洗一尽。
从这些诗文里,结合陈傅良的境遇,我们不难找出他为何如此偏爱赵园。古时的赵园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,我们无从知晓,只能从前人的诗句,结合自己的联想,勾勒出古时这座美丽花园的样子。
“十门园”可能就是赵园
那么,这座美丽的私家园林究竟在何处?带着疑问,笔者赴汀田街道金后村一探究竟。
站在汀田街道金后金润大厦的楼层上,金后村村支书金文富往岑岐山麓方向一指,古时的赵园很有可能就在那片区域,现在是一片黑压压的民房,几乎没有园林的任何痕迹。
每个村的大榕树乘凉处,大概都是村里的“政治文化中心”。向乘凉的老人们打听时,笔者获知一个重要的线索。一位长者称,虽然没听说过“赵园”,但知道这里曾经有个“十门园”,园林存留了好久,就在金文富书记刚刚所指的那片区域。更精确地讲,就在不远处杨伍侯庙至岑岐山麓的区域,如今已被一片乌泱泱的房子所覆盖了,恐怕任何遗迹都找寻不到了。
现年73岁的前党支部书记金文虎回忆,六七十年前,印象中的“十门园”是一片荒芜的大园子,乱石堆砌,杂草丛生,里面种了好多棕榈树,还有几十具稻草覆盖的棺材零散在空地上,显得十分阴森可怕,总面积约莫有三四亩。从位置看,与翠阴洞、宝坛寺、岑岐糖厂遗址挨得很近,而翠阴洞,村民唤作“宝坛寺洞”。
由此,笔者推测“十门园”曾经是一个规模相当的园林。为什么叫十门园呢?古人常以量词形容事物的大而多,“十门”很可能是指园内有较多景致,应该属开放式园林,即没有围墙。因岁月的流逝,花园逐渐荒芜衰败,最终消失殆尽。
村民建议我们再去找找村中90多岁的金培启老人,或许从他那里可以得到关于“十门园”的信息。金培启老人提到,年轻时候喜欢听鼓词,特别是听鼓词艺人赵岩儿说唱《大破山皇寨》,大意是写明朝时期金岙人金宝同带兵剿灭盘踞在山皇寨贼兵的情节,里面多处提到“岑岐”“金岙”“十门园”等内容,年月太久,很多已记不清了,但他对“十门园”的回忆基本与金文虎老人描述的差不多。
那么,历史上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的赵园,是不是人们口中的“十门园”?因两者位置基本吻合,笔者大胆推断,“十门园”极有可能就是古时的赵园,起码可以证明“十门园”是赵园的“后生”,但有待进一步论证。
赵园到底何人所建
“十门园”究竟是不是赵园暂且不论,我们再来谈谈与赵园关联密切的北宋皇族赵㞦。坊间传说,赵园系赵㞦为父亲赵抃建造的一座私家花园,供其享福。
笔者认为不大可能,从种种资料显示,它更可能是金岙当地赵氏建造的。
赵㞦,字景仁,衢州西安人。《宋史列传》卷七十五载:“㞦字景仁。由荫登第,通判江州,改温州,代还,得见。时已谢事,神宗命为太仆丞,擢监察御史。以父老请外,提举两浙常平。元祐中,复为御史。”
赵㞦的孝心是出了名的,奉养父亲的故事被传为佳话。北宋元丰二年(1079),其父赵抃以“太子少保”致仕。次年,任温州通判的赵㞦便把父亲从衢州老家接往温州赡养。在赴温途中,赵㞦陪同父亲游览天目山、雁荡等地,陪同游览的还有时任温州知州的石牧之。回到温州后,赵㞦将父亲安顿在自己的“公廨”里(类似现干部宿舍)。为了让父亲安度晚年,赵㞦在公廨里修建了一座戏彩堂。传说老莱子年七十还穿五色斑斓衣上堂作婴儿戏,故意仆地以博父母一笑,赵㞦此举是模仿春秋时楚国老莱子的故事。
赵抃对“塘岙先生”林石的孝行早有耳闻,特别是听闻其母戴氏虽已年逾百岁,身体依旧硬朗,十分好奇,便让儿子赵㞦带他到塘岙拜访。林石的出名,不仅在于学问大,他还是远近闻名的孝子。其父早逝,林石在塘岙父亲的墓旁筑了间屋子,取名“萱堂”,长年居此祭父养母。据说,林石的母亲活到119岁才去世,而此时的林石已年逾九十,依然遵守礼节,为老母居丧守孝。赵㞦的“戏彩堂”和林石“萱堂孝亲”的故事皆被后人传为佳话,其彰显的孝义在温州世代相承,还被编入词曲广为传唱。
赵㞦的孝行令人称道,但由此说赵园是由赵㞦建造、用来奉养父亲的观点,却是没有根据的。赵㞦来温任职是公元1079年,父亲是公元1080年来温、公元1084年离世,赵㞦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,并在距离自己工作30多公里的地方建一座宅邸花园侍养父亲。
赵园更大的可能还是金岙当地赵氏望族所建造的。
金岙现在虽然以金姓、蔡姓为主,但当时金岙有没有赵氏聚居呢?答案是有的。
唐宋之后,温州山水名声更显,宋代众多名人官员、宋室后裔欣然前来工作、定居、游玩。《瑞安县志》载:“本县赵氏有东郭和金岙二支,均系宋宗室之后裔。分布于塘下镇赵宅、鲍田镇及县城。”金岙赵氏应该是宋宗室后裔。据金文富所述,金后和金前目前虽然无赵姓人口,但早前金岙确实是有赵姓人居住过,后来不知何故,赵姓人逐渐外迁,现今村里基本无“原住”的赵姓人士。陈傅良还记录了这么一桩趣事,可为佐证。赵㞦听闻“东郭”有赵姓,也有跟自己一样是景字辈(赵㞦,字景仁)的族人,觉得很好奇,立即跑到“东郭”查证。当赵氏族人翻出族谱核对时,赵㞦发现其先祖竟与自己的衢州“西安”赵氏同出一脉,亦为赵氏宗室后裔,不由地喜出望外。
在温期间,赵㞦曾多次携朱履常(名朱素,时任瑞安县令)、林石(世称“塘岙先生”,北宋温州“皇佑三先生”之一)等好友赴金岙游玩,赵㞦在游岑岐山时留有一诗:“洞门乔木昼阴阴,洞穴嵌空透碧岑。偶约骚人同此乐,摇毫静坐发清吟。”在岑岐山翠阴洞至今尚存多处摩崖石刻,“赵景仁、朱履常、林介夫元丰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同游”及“辛未末伏后二日,履常遇介夫,来岑同游翠阴洞,成短诗,‘小洞隐遥岑,松萝翠复阴。游人曾不到,方信白云深’”,后者据考证是朱履常的原作。“元丰五年十一月”(1082)与“辛未末伏后”(1091),相隔9年,可以充分说明赵㞦曾与友人多次相约来金岙及岑岐山游览。
宋元以来,文人墨客造访翠阴洞、宝坛寺、赵园后,留下了许多诗文和石刻,但奇怪的是,从元代以来,却鲜少提及赵园,赵园像是销声匿迹了一样,这是为何?笔者认为,元朝灭宋之后,元廷对赵氏皇族赶尽杀绝,很多人被迫背井离乡,特别是赵氏皇族后裔刻意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和姓氏,以求生存。一切关于赵姓的痕迹被肆意抹去,赵园也可能因此更名,并逐步荒废,鲜有人知晓它曾是一座宋代私家园林,更鲜有人前来游玩,最终遗忘在人们的记忆中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,随着人口增多,房屋增多,人们渐渐在空地上新建了房子。后来由于房子越来越多,荒地也消失,关于赵园的遗迹亦荡然无存。
宋韵文化,闪烁于中华文明的历史星空,翠阴洞、赵园的印记,皆是历史留给今天的宝贵财富。像一位文史前辈勉励笔者那样,挖掘赵园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,“使命光荣,君之勉之”“上承两宋之赵园逸韵,下开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新面貌;物质、精神文化双提升”。赵园,宛如一幅细腻温婉的水墨画卷,缓缓铺陈在历史的长河之中,以其独特的韵味,诉说古时的风雅和精致。一切有关赵园的故事,只留在云山苍苍、斑驳树影里,有待后人慢慢发掘和捋清,还历史本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