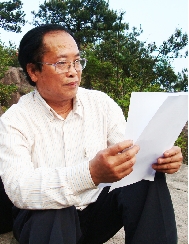回忆几件事
■陈思义
我新近出了一本书《曾为总编》,回忆在瑞安日报社的一些事。
说来话长。十年前《瑞安日报》十周年庆,报社的同事热切地说你老总编写一篇纪念文章吧。于是我写了一篇《曾为总编》,被发在十年报庆专刊上。就是这个,我想无不顺势把在报社几年的某些有意思的事,记录下来,附上报社同事的文章,编成一本书呢?
也就是十年前,我建了两个文件夹,名为“写”的文件夹,是我的回忆文章,名为“录”的文件夹,是我的报社同事的文章。应了“老年人往后看,青年人往前看”的古话,退居二线了,也该是往后看的时候了。后来电脑坏过一次,书稿还在。到电脑换代了,书稿被拷下来放在新机上。一下子十年过去了,书稿还睡在电脑里,还是没有丢了。今年的一天突然想起这事,打开电脑里的文件夹,重新把书稿“写”了一次,就编成了一本书。
十年后重新来“写”,容易多了,因为去年不小心跌断了一条小骨,一跌把我跌进了老人行列。还是应了“老年人往后看”那句古话,如今再作回忆就水到渠成了。我在《后记》里说,《瑞安日报》已走过二十个年头,其间我在报社近四年,却留下弥足珍贵的人生轨迹,我因此引以为豪。《曾为总编》的字里行间就有这种自豪感和幸福感,读者也会看出一种显扬和自信。卸任已十一年了,春来春去,《瑞安日报》还记得我吗?我对《瑞安日报》显然至今梦萦魂牵。
许多东西当你失去了就觉得珍贵了,比如青春,比如健康。不少事情过去了你才有所醒悟,比如读书的年头觉得读书苦,当走出校门进入社会,那大大小小的事情,拉拉扯扯的关系,才使你醒悟到原来读书的时候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。再比如上辈健在的时候你也无所谓,关照得多的是下辈,所谓“上孝下”,而一旦上辈都走了,你成了最大的一辈的时候你才醒悟,老得“抖抖动”甚至小便失禁甚至老年痴呆的上辈,对我们是多么重要。上辈在,才有孝的机会。上辈在,我们不言老。上辈是青春的参照物,参照物没了,我们会突然有一天感到一阵凉:我也老了。
人老了容易回忆,去年今日,人面桃花。今天我书房外的栀子花很香,想当年和一群报社的青年人下乡,也是这么的阳光,前面还扛一面瑞安报社青年记者的旗,路上见到水稻、温郁金、索面、野菜,就一一说给青年人听,自己也年轻了。回来写了一篇《青春做伴好下乡》,青春:春光明媚的日子,乃杜甫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诗意。人说这是一篇好文章,无非是说情真真意切切。
又想起王步宙,想起黄则强,想起阿维热,想起张增清,想起张曼新,想起毛晓宇,想起采访与报道过的人。最难忘采访王步宙,几位记者是坐“突突突”拖拉机去的,王步宙用的粉笔头和百宝箱,那一堆来不及盖到屋面上的瓦,家里的屋顶还在漏水,他累倒在教台上。一场场王步宙事迹报告会,我看女同志无不流泪,男同志大概也有十之一二流泪。男人有泪不轻弹,女人多泪为哪般?就是因为一些很“微”的东西太感人了。
又想起“2.24”空难报道,到现场看了,对生命的敬畏刻骨铭心。一连两天把消息排到报纸上又被通知撤下来的事一直记着,晚上八九点钟了,撤下了空难报道,报纸又不能开天窗,只得找东西补上去。忙碌了一天的同事显然有看法,那也无可奈何。空难发生在瑞安,发一个简短的消息为什么不可以呢?
又想起到北京,在报社的唯一一次省外出差是和北京上司说,办好瑞安报并未加重农民负担,给瑞安报全国刊号是顺乎潮流的事。说了一连串的数字,说了一个个的例子,我的温州普通话那天说得特别溜。
又想起设计师关于瑞安日报大楼的设计,征求我的意见。记得设计师是位美女,她问:什么设计风格?我答:像报社就是。她问:高度?我答:比旁边的市府大楼矮1厘米。美女设计师会心地笑了。
又想起我和管陶、陈志良,三个总编,都是书生,都是船快靠埠、车即到站的人,工作上可用一句话来评价:不用扬鞭自奋蹄。
《曾为总编》就说了这些有意思的事。书印出来,我就把书放在报社三楼的走廊上,你觉得想翻一翻,就去拿一本。书被拿光了,我会非常有幸福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