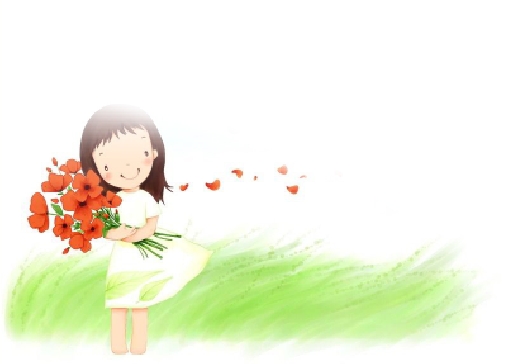光阴里的白裙子
■金春妙
日前,一群初中同学小聚,聊着聊着,不知怎地,聊到我身上。
静调侃说:“妙现在文章怎么这么能写?发表的每篇我都喜欢读,初中时候也没看出来啊!”
红说:“哪有?她以前就写得很好,我们都知道的!”她俩小声争辩我写作的源头,把我带进片片回忆里。
谁也没想过,爱上舞文弄墨源于一件白裙子。初中时,从来没想过以后的日子跟文字沾上边。只是一次,语文老师张小英让我们当堂写一篇《我的理想》。上交后,张老师把我的习作当做范文来读。具体内容不记得了,只记得张老师读到我穿着白色衣裙,风中衣袂飘扬时,同学们大概难以置信这个外表大大咧咧的丫头,笔下居然如此深情和诗意。一男同学脱口而出:“老师,肯定是抄的。”我既委屈又惊喜,委屈的是明明是自己写的,却被同学误解;惊喜的是恰说明我的习作在同龄中略高一筹。
后来每回忆起这个情节,总是伴着衣袂飘飘的唯美和浪漫。
老家在水乡林垟。弯弯曲曲的河流,高高低低的石桥,还有明清的牌坊与古屋。小时候跟弟弟吵架,难解难分时,母亲总是一跺脚:“吵吵吵,谁吵赢了林南的牌坊背去!”我们姐弟顿时噤了口,不敢惹母亲生气。我多想让母亲说,吵赢了做一件白裙子。白裙子成了我朝思暮想的对象。
家离学校并不远,每天上下学总要穿过老街——清朝遗留的一线天古街。房子相向而建,这家窗户一打开,可以握住对面窗户伸出的手。每逢雨天,屋檐下汇聚的雨流把时间拉得漫长。古街长长,街上有一个豁嘴女裁缝,手艺精巧。每逢经过店门口,我总是忍不住张望,迈不开步。拗不过我的固执,后来,母亲最终扯了几尺白色布料,把我领到裁缝跟前。豁嘴裁缝量了尺寸,对母亲说:“给她做一件荷叶袖的裙子好不?今年最流行的款式。”声音柔柔的,真好听!
等待漫长的半个月后,荷叶袖,裙摆镶着蕾丝花边的白裙子出现在我面前,美得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。
是否每个女孩都有一个仙女梦?又高又瘦的我第一次穿着质地绵软的白裙,飞扬在古朴又热闹的小镇,害羞又炫耀,风一吹裙子就会起波纹,衬着腰身一波一波荡漾,身后目光一片,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。但大多时候这条裙子像珍宝一样躺在衣柜里,不是隆重场合(比如吃摆酒),舍不得穿!等再次拿出穿时,却穿不下了。衣服还停留在当初模样,而我早已长高。惋惜和无奈填满往后的岁月,一切错过了,最美的年华!最美的裙子!
此后,有了各色的裙子,长的、短的、花的、素的,唯独没有白的,拥有的渴望也尘埃落定。有一些事物,初遇时太过隆重,反而走不到现实中来,比如理想,比如我的白裙子。
那么,有一种结局是否早就写好,如同年少时没有抄完的汪国真诗词,一落笔就注定它的不完满。只是小小的少年心尚参不透,缺憾是另一种拥有,就像纠结在光阴深处的白裙子,那么纯,那么真!
如今极力痴缠文字,是不是为了续接少年时的梦,还有梦中飞扬的白裙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