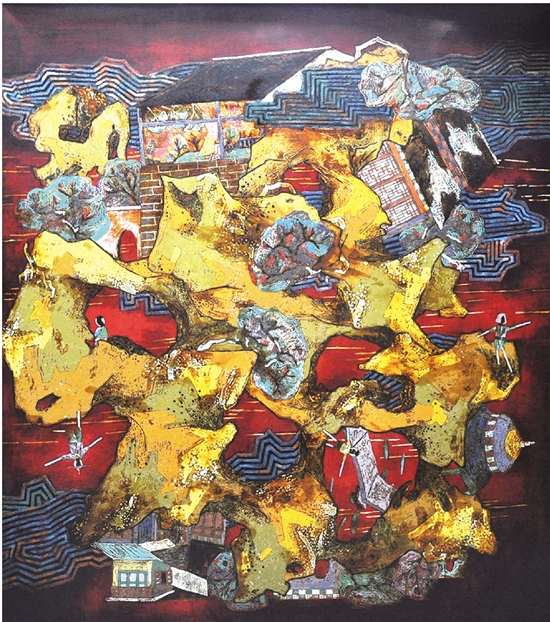走过仓前街
■余寿权
年前,温州市公布了第二批地名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名录,家乡的仓前街和另外三条街,榜上有名,我甚感欣慰。
仓前街是我的出生地。生于斯,长于斯,对古街上的每一条巷弄夹儿,每一处旮旯水洼,每一块古砖旧瓦,及其所承载的旧时光,我谙熟于心。己亥正月回乡祭祖那日,天空飘着毛毛细雨,行人稀少,路面湿润清净。我撑把大伞,漫步在久违而又十分亲近的街头,在水雾中顿感身心轻松清爽。
仓前街虽然没有乌镇、西塘那样的屋密弄深,但街道两旁高低不等,门面装饰各有花色的旧民居,也明显留有江南小镇白墙黛瓦的痕迹。街面上没有行道树,但各家门口凡是有空余的地方,总也摆着几盆或观叶,或赏花的植物,给古街营造着另一种生机勃然的氛围。那些个老街坊,或三三五五坐在临街的门槛底,喝着绿茶,嚼着芝麻糖、冻米糖、花生糖,啃着箬糕、松糕、双炊糕,讲讲笑笑。或身子在各自屋里,倚着门框探头相望的隔壁邻居,正在东山上西山落,扯着闲篇。他们有的曾是我儿时的玩伴,或他们的兄长、长辈。此番场景,跟门边新糊上的春联,屋檐下挂的红灯笼相映成趣,在蒙蒙的春雨中令我有似曾相识之感。
凡做了店面的旧房子,半开的那扇门上,照例贴着大大的红纸金粉的福字。福字下方不起眼的地方,另贴了一张红纸:“春节歇业,正月初十开门。”与我儿时不同的是,此时该满街跑着,嬉戏、放鞭炮,追逐打闹的孩童们不见了。在门口露脸的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,唯有他们才恋着这条街道,即便在新区买了楼房的子女,把那老城外的“乡下地方”夸出花来,也无动于衷。据说,我的母校“二小”,少了老街周边的生源,几乎成了“新瑞安人子女学校”。
当我撑着伞,走过老市委大院,走过瑞中老校区,驻足在最北端的永胜桥头,隔着雨丝,仓前街她那古朴儒雅,遗韵幽远的人文沉淀,她那通体馨香,书声悠悠的时空,已然不再。而身旁北濠河那随风荡漾的清流,那波光粼粼,充满诗意的水乡风貌,依然延续着古街的韵律。
东晋太宁元年(323),郭璞卜迁瑞安城,将县治安置在邵公屿,当时并未筑城墙,是有城无墙,“城”内仅“一街一河”。瑞安建造城垣始于南北朝的宋时,而且规模甚小,至元时城墙四周总长仅约800米。据资料记载,瑞安城最早的雏形,相当于今劳动巷、道院前街、衙后街及解放中路(劳动巷口至衙后街口)合围而成的地方。那时,还没有“仓前街”的概念。
随着时间推移,西岘山周边的海涂不断淤积,与邵公屿连接成片,也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,“建城”得到历代官府重视,瑞安城才得以不断拓展。“城内河道密布,呈三纵四横格局;有大小街道32条,依河成街,具江南水乡特色”。此时,仓前街才登上历史舞台,成了其中东南至西北走向的“一纵”。她的街头原有秀岘山门(在西岘山东麓),明朝时在此建有丰积仓,故名仓前街。循着街名,她也必定是与粮食储运有关。清末以前,在西河西侧有条纵向傍着仓前街的河,确实是一条运粮河,其向南流至望马河,向西北通向西门,其三条支河,分别沿第二巷、西大街、市街侧东与西河相通。遗憾的是,至清末时运粮河因久无疏浚,皆淤积成沿街排水沟渠。沟里流淌的水,来自于北湖,来自集云山,非常清澈,阳光下漂浮着些许蓝天白云,江南水貌若隐若现,仍然给人以舒适温和的感觉。到了1959年这些沟渠都被改为下水道,然后填埋,铺上青砖路面,成了仓前街的新雏形。
仓前街,长不过470米,宽亦只5米,但东西两侧却分布着十来条巷弄,拥有许多遗名至今的古迹。岁月漫漫,曾有许多披着文化霞光与历史色彩的人物,在此间信步走过,留下匆匆却美好的足迹。明代及以前的仓前街西侧有城里唯一的义仓(丰积仓)、陶尖殿(也称显祐庙)、蔡宅祠堂、孝节祠及天王寺等古建筑。到清代,东侧不仅有瑞安协营水师副将署及练兵的小校场,还有文史学家李笠的“横经室”藏书楼,及其同学——著名经史学者、教育家周予同的故居。民国初年,在仓前街的巷弄里,尚在上初中的李笠、周予同和另外几位同学陈骏、薛钟斗、林熹等人,组成学习小组,他们崇仰孙诒让、陈黻宸,秉承学习经书,必要通达史学的务实精神,篝灯研读,诗词酬答,成绩斐然,为他们走出仓前街,走出瑞安城,成为闻名于世的大家奠定了基础。
世居西门街的林去病,原名康宝,为了洗刷“东亚病夫”的耻辱,取笔名“去病”。他是瑞安红色革命的先驱,中共瑞安党组织的创始人,在从西门街经过仓前街,到东门外话桑楼,到乐清、宁波等地组织革命活动的路上,曾经飘洒过多少欣喜而神秘及至神圣的心情。百年名校瑞安中学,自1939年在仓前街西北端的节孝祠落脚扩充分部,培养出许多科学精英、学者大家、社会名流,走过仓前街并不宽敞却十分古老的街道,走向全国甚至全世界,如群星璀璨。如今,瑞中也已“择木而栖”,搬离古街去了集云山麓,其他古迹也随着世事变迁而消逝。
雨歇了。我收拢伞,抖抖水珠,隐约感觉若有所失。转而想,我所思所怜的出生地,不是上了重点保护名录吗?
至少在那儿肯定是能流芳百世的,仓前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