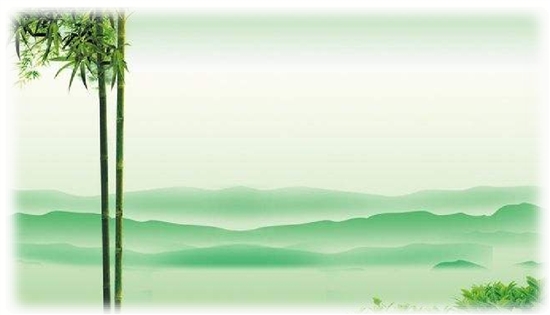筼筜山之旧名、
旧址辨析
■许小寒
瑞安今存地名中,有一处叫筼筜桥,说来颇为文雅——筼筜,乃竹名,指一种生长在水边的大竹子。《异物志》曰:“筼筜,生水边,长数丈,围一尺五六寸,一节相去六七尺,或相去一丈。”
既名筼筜桥,可知当年桥畔或植有筼筜,或是因竹近水而名筼筜。翻旧书查找,1988年出版的《瑞安地名志》中对筼筜桥作了两种解释,在“隆山乡”条目有筼筜村筼筜桥,注曰:位于白岩桥东向2公里处,村头有石桥一座名筼筜桥,据旧志载称,筼筜书屋在沙塘,为元季德基之所有,一为鲍端别墅,清鲍养初于沙塘之地种竹数百本,藏书为终老计,匾曰筼筜(竹之最大者)。因以名桥,村从桥名。
然而同一本书中的“桥梁”这一分类中,筼筜桥的注释又为:筼筜桥,在隆山乡筼筜村,明朝时,村西涂边盛植竹林,林边有高地称筼筜山,桥在竹林边,故名。
这两个筼筜桥的注释显然是同一处,但是桥名的由来语焉不详,或说是以筼筜书屋命名,或说是以林边筼筜山命名,自相矛盾。
明代官修地理总志《明一统志》中载:“筼筜山在瑞安县东八里,一名筼筜谷。山多产竹。”瑞安乾隆县志载:“跨官塘,通仙浃。”嘉庆县志载:“去城东八里。明处士季月泉隐此,多种竹,故名。”此后乡贤前辈提及筼筜山多以上述史料为据,认定筼筜山原是无名小山,因季氏植竹而得名。筼筜桥名是因筼筜山而来,而“筼筜”一名最先是季氏所起,前辈学者对此多无异议,只是为季月泉活动的时代作了纠正。季月泉,名初,嘉庆县志载明人为误,月泉实为元代人。月泉建筼筜别墅,后其孙又在别墅旧址上新起筼筜书屋,得诗句“ 明月照筼筜,清泉绕书屋”,这即是筼筜书屋的由来。
但从这些史料看来,瑞安县东八里处在今日筼筜桥村附近,而季氏祖坟(筼筜书屋旧址)在沙塘附近,二处相差甚远,跨在官塘上的筼筜桥并不依靠筑有筼筜书屋的筼筜山,则筼筜桥的“筼筜”何来?
又《瑞安地名志》释“君子石”曰:“位于市区东北4公里,民公乡仙浃虞北……宋儒林石讲学其下,人慕而称之君子石,石右有瑞云洞,华峰、翠峰,明处士季月泉隐居于此。”又有释“民公乡”下“西岙”曰:“在仙浃虞相北1.9公里。村北偏东有筼筜山,旧志载,明处士季月泉隐此。”——西岙即今瑞祥新区沙塘区域,村北偏东这座山在宋时称君子石,元后则因季氏家族易名作筼筜山,今仍是称作筼筜山或君子石的。
筼筜山既在东北位置,则与县东8里处描述不合,不过旧志中亦载“东河东,去城东8里”有筼筜河,筼筜河中又有筼筜桥、杨家桥、中岙桥、云聚桥等桥,可见筼筜山、筼筜河原在一处,今已填了部分,保留的河域与塘河相通。《明一统志》成书之时晚于筼筜书屋百来年,但其中只记载筼筜山(筼筜谷)在城东,而无有筼筜书屋的典故,却到了清时嘉庆县志时才出现张冠李戴,及至《瑞安地名志》同一处又有两处矛盾的解释,故此后人皆误会筼筜桥因筼筜书屋得名。
而且筼筜村边高地筼筜山的得名,也并不若地名志所谓的是在明朝,有南宋著名文学洪迈著作《夷坚志》中甲志卷七《金钗辟鬼》为证。《金钗辟鬼》讲述的是瑞安县筼筜村村民张七妻遇鬼的故事。《夷坚志》虽多神鬼之说,但作者取材甚广,从其文中可考证宋朝的社会文化、民情风俗、轶闻掌故等史料,亦能证明筼筜村在宋时已有之,且村边果然有山,此山应是今已消亡的筼筜山。
故此实有两座筼筜山,瑞安县东筼筜山是今筼筜桥位置,县东北筼筜山即君子石,今瑞祥新区位置,而筼筜书屋的旧典故和筼筜桥是毫不相干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