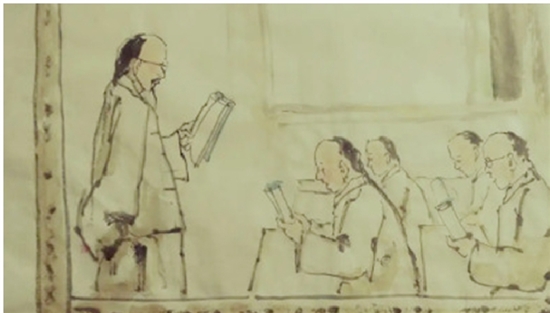这件事发生在明末清初的瑞安城。公元1644年,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,崇祯吊死煤山,明亡。吴三桂引清兵入山海关,李自成败退北京,清兵入京建立清朝。翌年,清兵攻克南京,弘光福王南明政府被灭。第三年,即清顺治三年,清兵进军浙闽。同年七月十四日,清兵三四十骑进瑞安县城,全县入清朝版图。
明末清初瑞安的三任县令
明崇祯十六年(1643),福建莆田人张岳到瑞安任县令,当时明王朝风雨飘摇,瑞安常受来往于闽浙间的军队骚扰,浙闽间各县疲于无度的军需供应,但张岳不畏强暴。明长洛王在瑞安要征民夫千名,全城不安,张岳单骑往见,讨价还价结果只以数名民夫应付。
清顺治三年四月粮荒,张岳设法劝当地殷户赈济,并反对压抑米价,使积粮者出米,外地闻讯亦运米来瑞,米价稍减。七月十四日清兵来瑞前,张岳召集乡绅来衙,以所存库银七百两托管,以应付急需,自己葛巾回闽。
清军入瑞,瑞安县首任县令是随清军南下的罗万象,江南人。他到任后善于调理民食和南下过境清兵的粮草。乡绅以张岳遗留下的库银加以补助。同时,罗万象设法使过境清兵绕城而过,避免入城惊扰百姓,城内稍为安定。但第三年,罗万象被调离。
接任的县令叫宁复雅,做派与张岳、罗万象完全两样,实施民族歧视和高压政策,强征暴敛,加上当年遭水旱灾害,酿成饥荒,矛盾叠加,民怨沸腾。从这三任县令的施政来看,宁复雅如能照前两任那样,注重安抚百姓,或许不会导致即将发生的变故,或使变故的程度减轻。
瑞安城发生“负刍之祸”
所谓“负刍之祸”,指的是瑞安西部山区饥民进城夺粮的事,统治者当然认为这是“祸”。事件的根源应从明朝的长期全国性缺粮说起。有人说,明朝覆亡的主因不是清兵入关,而是长期天灾人祸酿成的粮荒。明朝近280年的历史中,全国几乎水旱天灾不断,中后期越发严重,北方更加剧烈,加上政治腐败,民不聊生。李自成、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几乎全是被饥荒所逼的饥民。而我们地处江南水乡的瑞安也经常遭受水旱天灾而频频发生粮荒,西部山区的粮荒尤烈。
在明崇祯后期,湖岭山区一带的饥民在一位名叫陈世亨的读书人带领下,已经做好到县城去夺取官府粮仓内的粮食来活命的准备。后来因为崇祯吊死,李自成败退,清兵入关,形势剧变而暂时停止行动。在张岳、罗万象两位县令执政时,粮荒稍缓,他们伺机观察。到了县令宁复雅执政时,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突然尖锐,便点燃了他们进城夺粮的火焰。当年十月,陈世亨率部分饥民混进城内埋伏,自己带精干队伍事先买通县衙的门子,假扮为清兵马队运送草料的民夫进入县衙,约定时间每人头裹白头巾为记号,集中出动抢夺粮仓粮食。但因有人告密,事情败露,陈世亨等进入县衙的白头巾队伍被捕。
清兵在全城搜捕其他人员,温州清兵主帅即派兵南下,准备“屠城”(扩大目标大肆屠杀平民,此前的“扬州十日”和“嘉定三屠”就是先例),全城惊恐。幸有温州官府中的个别官员事先通知瑞安城内官员和士绅,四处奔走劝阻清兵主帅。“屠城”未行,仍逮捕城内数个与陈世亨有关系的人来作“替罪羊”。其中就有陈世亨的塾师陈昌言,罪名只是夺粮首领陈世亨的老师,最终被杀害。
陈昌言是位正直的塾师
清初瑞安著名的学者朱鸿瞻,也是陈昌言的学生。从朱写的《陈圣可先生传》,我们基本上可了解这位当一生塾师的陈昌言是位正直的塾师。文章称:“先生字圣可,隐居瑞安岘山之下,以文行勖后进。邑之学者多师尊事之。孝亲、友于兄弟,与朋友以诚,为文词朴率而典则,笑言不妄。智识明达,不信佛老之学;崇祯间,士大夫佞佛尤盛,先生为《著孔篇》(一作编,朱鸿瞻著,陈作序)……揭其卷首曰:‘士绅佞佛,甚为可忧。’不数年,遂有甲申之变(即崇祯十七年,明亡)。时人始信其言。弘光以后,先生幽居愤闷,一发为诗。顺治丁亥(1647)冬十月,邑有‘负刍之祸’,平(定)是难者,夷及平人(民),先生亦不幸遇害,年五十八……”从以上《传》中,后人知道陈昌言只是一介儒生,一介布衣,一世塾师,隐居山下,以自己德行文才教育乡里子弟,受到当地学者的尊敬。只不过对时局变化的愤闷,写了几句诗和一名学生为民众饥荒舍命夺粮,便受到株连被杀,何罪之有,却成为冤魂!
陈昌言的诗集也难脱厄运
陈昌言无辜被杀百多年后,正是史家所谓盛世的乾隆年间(1736—1795),清廷要编《四库全书》,通令全国,广泛征集民间书籍(稿)。乾隆三十八年(1773)正式开馆。当时浙江进献书籍数为全国第一,我们瑞安的林露(探花孙希旦的妻兄)任杭州教授,也参与进献书籍的校阅。陈昌言的诗集《山居草》(之前,瑞安人知道诗集书名的人不多),经过县、府、省三级层层“校阅”后也送到“四库全书”馆“校阅”大人们的案前。结果命运如何呢?再过了145年,到民国初期才得分晓。据当时的《北京大学图书目录·国学门·清史资料整理会刊》称:“乾隆四十八年(1783)九月,红本处(专门查检处理禁书的机构)查办《应毁书目》一册,前后凡7次,共计76种;续办4次应毁书10种,内第6种中有《山居草》一本,为明末陈昌言所撰古今体诗,诗多感慨,应毁。”从以上数十字中,后人才知道陈昌言的一卷诗集名称是《山居草》。好端端的诗集起码是吾瑞史料,却在作者被杀的百多年后,送到京都借编汇中华传统文籍集成时,遭毁,至今匿迹。
从本文的一个塾师和他的诗集的遭遇,不难窥见社会变故,局部地方的动乱,与当地施政者的关系;更可窥见就这么一本“多感慨”的诗集,也免不了“查办”“禁书”者们的“眼睛”。《四库全书》在成书的同时,有多少如《山居草》一样的书籍,遭遇《山居草》的厄运?可见嬴政“焚书坑儒”的屠刀,数千年来一直没有闲着,在乾隆时又被派上了大用场,竟连偏居海隅一角的小小瑞安县城也被“带携”着了,岂是“呜呼哀哉”四字所能了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