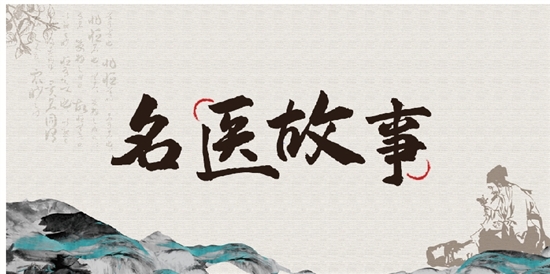郑作新(1318—1388)字谷谦,元末明初时期瑞安名医。他出生的时代,正值元朝蒙古贵族统治下的动荡岁月,自宋室灭亡后,各地抗元斗争此起彼伏,一直没有消停过。到了元末,民族矛盾更是空前激烈,瓯越大地烽火连天,生灵涂炭,民谣“瑞平当路走,东瓯做战场”,指的就是这个时期。
郑家祖居福建,后来迁徙至温州,在平阳横河(即今瑞安孙桥)居住。不久,又移居瑞安县城永丰街。这里紧傍丰湖,东接七铺温瑞塘河,风光秀美,景色宜人。郑作新在临街处开了间诊所,依靠看病行医维持生计。
封建社会医生的地位不高,跟耍手艺、走江湖的人差不多,被视作末流。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,郑作新从小就好学上进,本想靠寒窗苦读,考取功名,也好光宗耀祖。但元统治者把温州人民列为最低等的“南人”,实行种族歧视和高压政策,肆意盘剥奴役,郑作新是伴随着战乱与苦难长大的。虽然元顺帝至元六年(1340),朝廷下诏恢复了科举,但温州一带,能考取功名的人少之又少。郑作新秉性耿直,志存高远,平生不屈于非义,对元朝的黑暗统治,一直心怀不满。他觉得既然科考路塞,不为良臣,就做个良医,倒不如弃儒习岐黄,也好拯民于病痛苦难之中。
从此,他悉心钻研医学,孜孜以求,经常通宵达旦,秉烛夜读,遍览医家典籍,穷究经言,探寻古训,做到融会贯通。经多年不懈的努力,终成邑内最负时望的名医。他坦言“读书要究观大义,于医必克世其业”,决心把治病救人当作终生不渝的事业来做。
他宅心仁厚,怜贫恤苦,“人以病告,则不惮寒暑霖潦而拯视。”
有一次,邻居妇女夜间起床,突然昏迷倒地,丈夫大惊,急叩郑家大门呼救,把周边的人都给吵醒了。郑作新当即披衣而起,急急地赶过去施救,却见那妇人早已自行醒来。原来,她只是气血不足,一时昏迷并无大碍。见此情形,丈夫深感内疚,连声说对不住。郑作新却坦然一笑,“未尝责其报者”。
至正年间,浙南一带曾遭受过特大的飓风与海溢,潮水退后,疫情四起,天灾人祸,接连不断。很多时候,郑家医舍内总是一拨又是一拨的,挤满了病人。这可苦了郑作新,整天忙不停歇,常常连饭都顾不上吃,直累得心力交瘁,疲惫不堪。为此,他不由得慨叹:“大兵之后,必有凶年,眼下病患如此之多,为医者即便拼尽全力,也是无可奈何啊!”
来求诊的大多为穷苦百姓,据志书所载,郑作新对那些“或贫穷力不能致药者,请贷皆勿吝。我县受其惠者实众,远迩莫不仰慕欣羡之”。他不仅医术超群,而且医德高尚,为人正直,急公好义,在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。“邻居有争吵众不能平者,即喻以理或折以辞,无不慰悦。”别说是邻里之间,就是整个瑞安县城内,只要一提及郑医生的信义德行,没有一个人不佩服的,大凡民间有调解不了的事,只要请郑公出面,往往都能迎刃而解,众人有口皆碑,其恩德远播,载誉乡里。
据史载“元末兵燹之后,当道者以美官崇秩,笼络才俊”。瑞安州官久闻郑作新的大名,便派人去请他出来做官,以辅助地方治理。不料却被一口拒绝。来人大惑不解,对郑作新说:“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呀,上峰那么看重你,请你出来做事,你怎么就不识好歹呢?”他欲强之以官,郑作新就是不肯,退而谢之曰:“功名富贵如浮云,继志在我老死于医足矣!”
那人讨了个没趣,只得怏怏而返,告知州官说郑某不识抬举,竟拒人于千里之外。这个州官倒有见识,非但没有怪罪郑作新,反而打心底里钦佩他的正直,就没有再刻意去追迫。但他仍坚持要举荐郑作新,为表达诚意,便亲自登门拜访,向郑言明事理,告以心迹:自己已向上司请准,授予州医学正,好让他居官治其职事,为更多病患者施医服务。
郑作新见对方情词恳切,深受感动。再说就任州医学正,也不悖自己精医惠民的初衷,于是便欣然应允,同意即日赴任。学正是元、明时代地方政府的学官,掌管生员教育。据有关记载考证,郑作新是瑞安历史上最早就任州医学正的医官,可见早在600多年前,瑞安就有医学教育了,这与清末陈虬首创全国最早的新式中医学校——利济医学堂,是否也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呢?
郑作新弃儒精医,尤其是就任州医学正之后,有所著述,但世事变迁,年代久远,其著作均已失传。他卒于明洪武二十一年(1388),次年葬于万松山麓楼隐寺西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