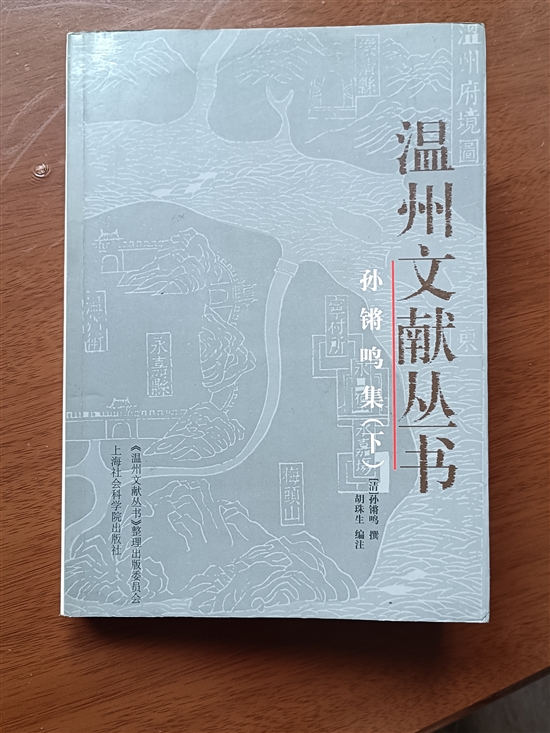孙锵鸣与其兄孙衣言、侄孙诒让和同邑黄体芳、黄绍箕父子是瑞安近代著名的学者、政治家、教育家,他们毕生基于民族振兴、国家富强、人民安居的夙愿,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传承、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重振永嘉事功学派学术的雄风,为家乡教育事业作出贡献。笔者特以孙锵鸣晚年学英语的小故事,作为今年教师节的小礼品,与大家分享。
孙锵鸣,生于前清嘉庆廿三年(1817),距离道光二十年(1840)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、闭关锁国的国门被英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、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《南京条约》仅仅20多年。就在这20多年中,他四五岁(以下均为周岁)即由其父口授儒家经籍,每日严加督课,全心倾注在科举学问之中,8岁能文,18岁中举人,24岁(1841)中殿试第34名进士,钦点翰林院(培养准官员的学府)庶吉士,28岁授翰林编修,30岁任礼部会试第11房同考官,32岁典试(主持广西乡试),后留任广西提督学政,任满,36岁,朝廷命他在原籍瑞安会办团练捐翰,历时9年。其间,朝廷又将他的职位从学政升侍讲,再升侍读左右庶子,再升侍讲学士,直至侍读学士。45岁回京,翌年任兵部武举会试内榜副主考官。47岁,朝廷勒令他着即休致(退休)。
孙锵鸣罢官回乡后,仍一直悉心治学和从事教育。61岁,被聘主掌(南京)金陵书院和惜阴书院,后又主讲上海龙门书院。70岁(光绪十三年,1887)时,身兼上海龙门、南京钟山、上海求志、温州肄经四大书院掌教。门下著录学生数千人。就是这样一位平生始终与中华传统文化典籍打交道,而且深有造诣、国内学界著名的老文人,竟直面现实,对满清政治家一向鄙视而又被欺凌的所谓夷邦的英语发生兴趣,且积极推崇、学习。
关于孙锵鸣晚年学习英语的具体记录,《孙锵鸣集》(胡珠生编注,列为《温州文献丛书》)中只有一篇,是抄写在龙门书院读书日记簿上的读书笔记。就是这一页记录,却让一百多年后的笔者初读时,闹出大笑话:因为这页笔记的抄录者专抄称谓的英语单词的中文注音,标题为《西语记音》(当时所称的西语系指英语),如父(法特)、祖(搿蓝法特)、母(墨特)、外祖(墨特纳而搿蓝法特)、兄(爱而头白勒头)、弟(盈搿欧白勒头)、姊(爱而头昔司偷)、妹(盈搿欧昔司偷)等。笔者初看时,不禁暗自发笑说:看来这位瑞安大学问家先辈,初学英语也会像我们儿时那样,贪懒、贪便,不认真学拼音,只把中文读音记在英语单词下面。如父后注上“法特“读音,进而反自以为是,还批评起这位老人读音也注错了。父的英语father,应注“法蚕(方言音)”而非“法特”。
后来经过查考,才知道笔者真是十足的“读书呆”。原来,清道光和光绪年间国内没有系统的语法书或正规词典,学习者依赖的是由早期通事(翻译)或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商人编写的《红毛话》等小册子。中国人在国内学习的英语,是一种基于汉语方言注音、语法结构中文化的“洋泾浜英语”的雏形。所以,孙锵鸣注音的“法特”等,是基于当时他听到的发音用汉字记录下来的,而且他的方法也非常典型:他用中文的思维(如“祖父”是“父亲的重复”)去理解和分解英语词汇(grandfather),这也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初学英语时的普遍策略。更可贵的是,他还对此进行扩大与类比,可见他已经从学单词进而深入到英语语法领域!百多年前的老人竟比笔者先知先觉几百倍,怎能不令我为之前的笑话而汗颜!
不仅如此,孙锵鸣掌教龙门书院时,还敢于冒当时顽固士大夫之大不韪,为汲取西方科学知识,“慨然言于(请求)苏松太分巡道(江苏的一个道的长官),移取(江南制造)局译的西籍(西方科学书籍)一分,存院,俾诸生纵阅。”龙门书院原本是专授中华传统文化所谓国学的,可见这位70多岁的老人晚年学西语,绝不是赶时髦、出风头,而是在书院里带头提倡以学西语为工具,还想亲自多读些书,深入地了解西方科学知识,做诸生的榜样!
由此再联想到吾瑞学人中的精英,大都是这位老人的亲属、姻亲的后辈,如孙诒让、黄绍箕、项湘藻、项申甫及林调梅、蔡华卿等。光绪二十二年(1896)和二十五年(1899)在瑞安这个小小的县城,举数家人的财力和数人的学识,在全温州率先创办学计馆(相当于现在的理科专科学校)和方言馆(相当于现在的外国语专科学校)。宣统元年、二年清廷的留学生廷试中,瑞安竟有项骧(从学计馆走出来)中廷试复试一等第一名,得进士,授翰林院编修;林大闾得留学生廷试初试第一,得工科进士,授翰林院编修;林大同、黄曾铭、薛楷等各得留学生廷试进士。这不能不说孙锵鸣的榜样作用对这批后人在思想、学术上产生的深刻影响!